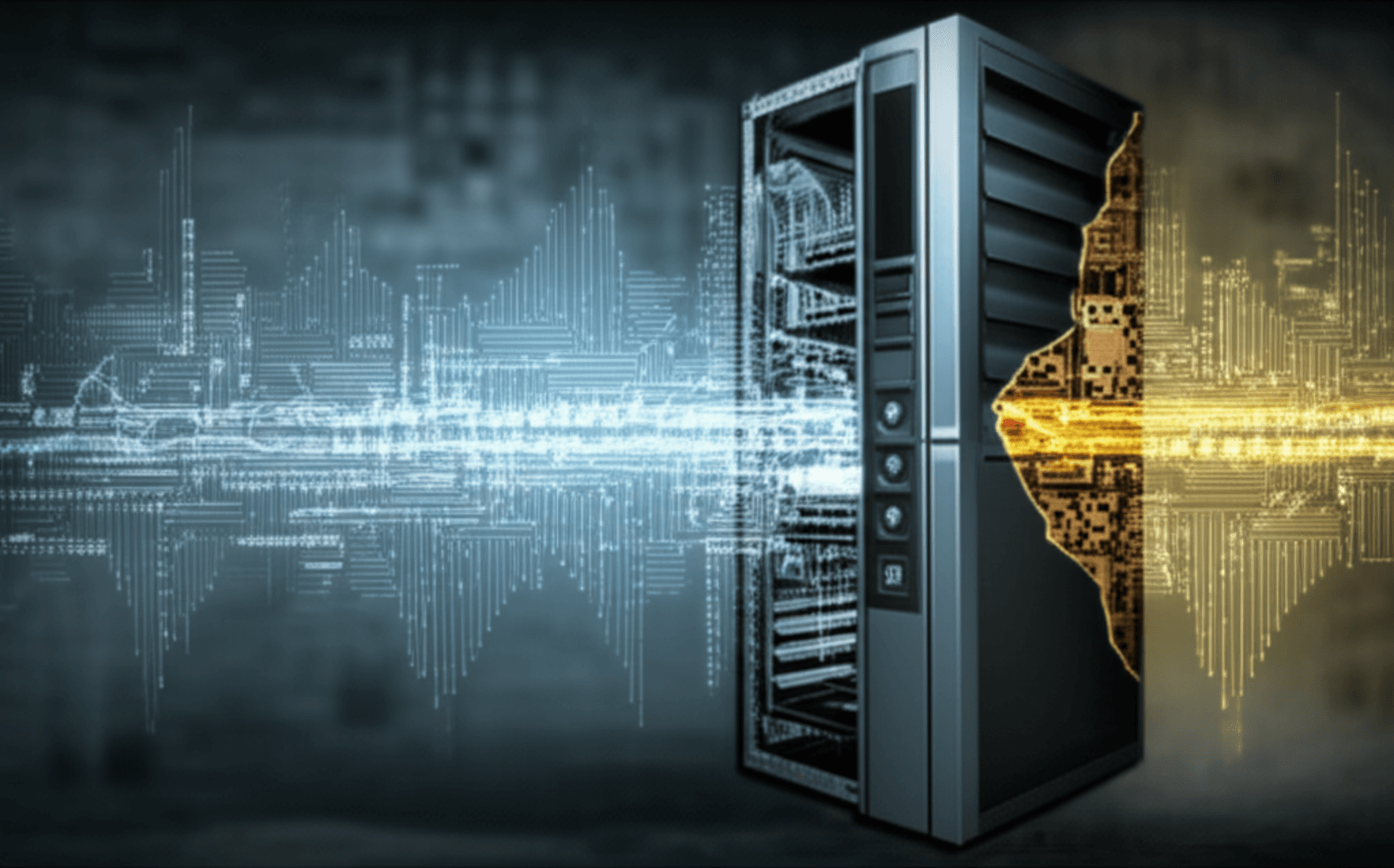
台灣社會似乎每隔一段時間,就會被捲入一場關於核能的集體高燒,而即將到來的核三廠延役公投,無疑是最新一次的病徵發作。
然而,若我們將視角拉遠,會發現這場看似非黑即白的能源對決,其本質並非單純的擁核與反核之爭,而是一面映照出台灣數十年來「治理失靈」的照妖鏡。
我們面臨的真正危機,不是電力供應的缺口,而是一個更深層、更致命的困境:我們成功引進了全世界最複雜的能源「硬體」(核子反應爐),卻始終未能為其開發出一套穩定、可信賴、且能與時俱進的「社會作業系統」(Social Operating System)。
這個作業系統,包含長期的政策穩定性、跨越黨派的社會共識、透明的溝通機制,以及對未來世代負責的承諾。
當前的辯論,無論正反雙方如何言辭激烈,都只是在這個充滿漏洞、頻繁當機的舊系統上,徒勞地執行著相互衝突的指令,最終導致整個社會的效能癱瘓。
要理解這套失靈的「社會作業系統」,我們必須回顧核三與核四這對命運迥異的兄弟。
坐落國境之南的核三廠,是威權時代的產物,它代表了那個「硬體至上」年代的技術巔峰。
當時的治理模式單純而高效:由上而下,技術官僚擘劃藍圖,國家意志強力推行,社會溝通與公民參與等「軟體模組」並非必要。
因此,核三廠得以在一個相對封閉的環境中順利建成並穩定運轉四十載,成為台灣經濟奇蹟的功臣之一。
然而,三十年後,當台灣的民主化浪潮風起雲湧,同樣的治理邏輯在核四廠的建設上,卻釀成了一場史詩級的災難。
核四放棄了統包模式,改為自行分包採購,這個決策本身就是對自身軟體整合能力的過度自信。
當這個被譏為「拼裝車」的硬體計畫,遭遇到政黨輪替的衝擊、倉促停建復工的政治干擾,以及民間日益高漲的不信任感,其結果便是系統性的崩潰。
耗資近三千億卻未發一度電的核四,如同一座昂貴的紀念碑,永久封存了台灣企圖用舊時代的硬體思維,去應對新時代複雜社會需求的慘痛教訓。
如今,核三公投的辯論,宛如昨日重現,再次凸顯了這個失靈系統的內在矛盾。
正方代表翁曉玲委員高舉「救命的電」與「乾淨的核能」大旗,憂心火力發電帶來的空污與健康風險,這反映了民眾對於穩定電力和生活品質的「硬體需求」,是極其務實且急迫的焦慮。
她的論述,像是系統發出的「電力不足、空污超標」的緊急錯誤代碼,要求立即解決眼前的問題。
另一方面,反方代表林子倫副執行長則從「安全不確定性」與「成本不確定性」提出警告,強調核廢料處理是債留子孫的道德風險,並指出再生能源才是國際主流趨勢。
他的觀點,則點出了「社會作業系統」的核心缺陷:一個無法有效管理長期風險、缺乏世代正義考量、且與全球主流趨勢脫節的陳舊框架。
這兩方看似對立的論述,實則是在同一個失靈的系統中,各自解讀著不同的警訊,卻沒有一個更高層次的機制能夠整合分歧、尋求共識,導致社會能量在無盡的內耗中被消磨殆盡。
在這場治理危機中,核廢料議題無疑是吞噬一切信任的「黑洞」,是系統中最深層、最無解的Bug。
所有關於核能的討論,最終都會撞上這堵高牆。
芬蘭能夠建成世界首座高階核廢料最終處置庫,其成功的核心並非卓越的工程技術,而是他們花費數十年時間,精心打造了一套以信任、透明、公民參與及地方否決權為基礎的「社會軟體」。
反觀台灣,核廢料處置長期由政府與台電主導,決策過程充滿黑箱作業,公民參與往往流於形式,這種由上而下的治理模式,徹底摧毀了社會信任。
信任的崩潰,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:因為不信任,所以無法解決核廢料問題;因為無法解決核廢料問題,任何關於重啟或延役核能的討論,都顯得不負責任,從而進一步加深了不信任。
在這種情況下,本應作為民主補救措施的公投,也被異化為撕裂社會的政治賽局,它讓複雜的能源政策被簡化為口號式的對決,卻無助於修補早已蕩然無存的信任基礎。
隨著AI革命引爆新一輪的電力需求焦慮,台灣再次站在了能源政策的十字路口。
8月23日的核三公投,與其說是對一座老舊電廠的未來進行投票,不如將其視為對台灣社會治理能力的一次總體檢。
我們是否已經準備好,去面對比電力短缺更嚴峻的挑戰——重建一個值得人民信賴的治理體系?核四的廢墟與核廢料的僵局,不斷地發出警告:若沒有一套運作流暢、能夠凝聚共識的「社會作業系統」,再先進、再強大的硬體,最終都可能成為撕裂社會的根源。
這次的投票,不該只是選擇「同意」或「不同意」,而是我們共同反思的起點:台灣是否擁有足夠的社會智慧與政治勇氣,去為我們失靈的國家治理作業系統,進行一次徹底的更新與重灌?這個問題的答案,將遠比公投的結果,更深刻地決定台灣的未來。